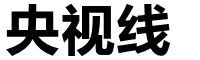1986年7月5日,我连续在陕西卫生报发表了三篇“防病于未然”文章,从那时起,就开启了我此后大半生对中医药膳与“治未病”理论的执着探索。这其中有很大的原因,是临床困境的逼迫:当时有不少辗转而来找到我,病情已然危重的患者,脾胃功能极度衰弱,古人形容“胃气已败”,再好的方药,若不能被身体吸收运化,亦是徒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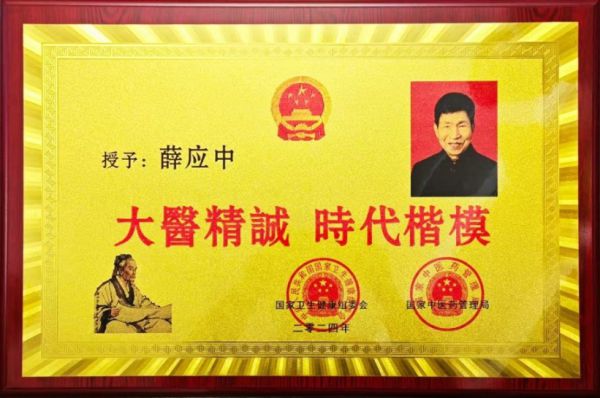
当时,我就开始构思药物加食疗的方法来治疗疾病。
脾胃是后天之本,气血生化之源,才是治病救人的“开路先锋”。倘若连米粥都难以运化,何况性味具有偏性的药材?于是,一个念头也愈发清晰:在投以汤药之前,或之余,是否应先想办法“唤醒”他们的脾胃?用什么唤醒?
既然汤药难入,那能否借助每日都离不开的饮食?许多食物,本身就有药的特性,它们性味多较药物平和,更易于被虚弱的身体接受。而这,正好与我之前思考的“治未病”“防病于未然”理念相契合,时日久深,我就积累了五十多例不同病情的药膳验方。
后来经过不断的探索,相当多的患者持续用药膳调理病情,尤其是现代医学所谓的癌症、放化疗、结扎、剖腹产等手术体质虚弱后,以及不想服中药的患者食用药膳后,效果相当显著。
直到现在,还有相当多的病人不愿服中药,需要用药食同源的药膳去治疗。最关键的是治疗脾胃和各种不同类型的后遗症时,尤其是有一些急功近利的人,没有经过临床辩证实践而乱用廉价药膳而导致病情加重。如有需要食用药膳的人,一定要求助有经验的医生指导,希望大家谨慎选择,不要随意乱食用药膳。
1
“夫为人子者,不可不知医;知医者,不可不知食。”古人之训,揭示了饮食与健康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药膳,这门根植于中华文明、融合了中医药理论与烹饪艺术的独特学问,远非“药食简单相加”,而是“医食同源,药食同功”中医思想的深刻体现。
一膳之中,可兼顾祛邪与扶正。它如细雨润物,不显山露水,却能在日复一日的滋养中,筑牢正气,削弱病邪滋生之土壤。使人于不知不觉间,精神渐充,体力渐旺,抵御外邪之力日增。
天下万物具有寒、热、温、凉“四气”与酸、苦、甘、辛、咸“五味”,人体之疾,本就源于阴阳失调、气血失和。所以药膳之妙,在于借食材天然偏性,以纠人身之偏。药食两用之材,其性多缓和不峻,既可缓缓纠正身体之偏,又无过度干扰之顾虑,适合长期调摄。
而人体健康与自然环境是一个有机整体。因此,饮食调理必须顺应四时阴阳变化。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,药膳亦随之调整:春日疏肝健脾,夏日清热祛湿,秋日滋阴润燥,冬日温补肝肾。此即“法于阴阳,和于术数”在饮食上的具体化。
2
药膳于慢病调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辅助作用。比如现代医学所谓的慢性疾病,如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冠心病、慢性胃炎、虚损性疾病等,其病机多错综复杂,常呈现“正气已虚,邪气留恋”的特点。此等痼疾,非若外感急症可一剂而愈,其治疗犹如抚育幼苗,需耐心与细水长流般的持续滋养。
当身体已出现失衡,或疾病处于胶着状态,药膳在此时进行干预,有助于防止其深化与发展。药膳于此阶段,通过温和的食养,帮助机体恢复气血,填补疾病过程中的消耗,加速元气复原;又能清除余邪:温和化解残留的病邪(如余热、痰浊),帮忙扫清战场;还可强化薄弱,针对病变所涉脏腑,进行重点调理,增强其功能,助力抵抗侵袭。
患者见肝郁之象(如情绪抑郁、胸胁胀满),即以疏肝理气之品调饮,防其乘脾土致消化不良,或化火伤阴;见脾虚之兆(如食欲不振、大便溏薄),即投健脾益气之食,固守中焦,防气血生化乏源,百病由生。
例如,用枸杞、女贞子呵护肝阴,以茯苓、薏苡仁健脾利湿减轻肾负担,用沙参、麦冬滋养被损伤的胃阴。这是一种立足整体、温和而根本的修复策略。此时药膳之用,犹如堤坝之微修补漏,成本最小,而收效很大。
3
药膳是中医“治未病”思维最日常、最平实的实践。它不待疾病已成而治之,而是在身体初现微小失衡时,便通过饮食悄然调和。对于亚健康状态的调节,如缓解疲劳、改善睡眠、调节情绪、增强免疫力,药膳以其温和、持久、易于接受的特点,也展现出巨大优势。
医学之最高境界,非“挽狂澜于既倒”,乃“防患于未然”。此即中医传承千载之“治未病”智慧精髓——未病先防,既病防变,瘥后防复。药膳,以其源于自然、契合医理、温和持久的特性,承载的不仅是营养物质,更是中医“整体观念”、“辨证论治”、“治未病”的智慧,是对患者身心全面的关怀与滋养。药膳是中医“上工治未病”思想最生活化、最普遍的实践。它通过每日三餐,潜移默化地调理体质,培育正气,筑牢人体自身的“防御长城”。

4
我在很多文章中提到“药源性伤害”,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回应。西药多由化学合成,成分单一,药力强劲,性多峻烈,用中医学的理论看来,可视为一种强烈的“外源性偏性”干预。此偏性虽能在一定情况下纠正病理状态,比如现代医学所谓的消炎、降压、降糖、抗凝、抗癌等,然而也易于打破人体原有之精密平衡,伤及无辜,导致新的失衡。
“脾胃为后天之本,气血生化之源”。药源性的伤害首伤脾胃。药膳调理,首要便是固护胃气,健脾助运。通过精心配伍之膳食,唤醒脾胃功能,保障气血生化有源,为全身修复提供物质基础。此乃“留得一分胃气,便有一分生机”之理。于患者而言,了解此道,便是在接受必要治疗的同时,掌握了一项主动进行自我养护、提升生活质量、减轻痛苦的宝贵技能。
药源性伤害应该不是医者本人的意愿,它是药物固有偏性作用于复杂人体后,难以完全避免的代价。在此领域中,药膳之学,以其“食药同源、性味平和、调理整体”之特质,可以展现出非凡的“匡正救偏”之功能。
药膳食性平和,少偏颇之弊:药物性味多偏,用力峻猛,旨在攻伐,故需中病即止,不可久服。而食材(及药食两用之材)其性相对平和,适于长期调养,缓缓图功,无过度干扰人体之虞。
药膳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使人悦享其味。“良药苦口”常使人生畏,而“良膳可口”则让人欣然接受。药膳讲究“食借药力,药助食味”,通过巧妙配伍与烹饪,化养护之功于美味之中,使人防病于享乐之间。此乃最高明的医道——让护持健康成为一种愉悦的生活方式,而非痛苦的负担。
与药物之峻烈相比,药膳最大优势在于其平和性与可持续性。它在修复药源性伤害中展现出来的匡正之道,为深受药源伤害所困者,打通了一条温和有效的康复之路。
5
药膳更有助于在术后固护生机。手术之后,患者身体呈现一种特殊的“亏虚”与“紊乱”交织状态,其核心病机可概括如下:
第一就是气血亏虚。此为最直接、最核心的损伤。手术过程中,失血耗液,直接导致血虚;麻醉、手术操作、疼痛恐惧等,剧烈消耗人体功能活动,严重损伤气(尤其是元气、宗气)。故术后患者常呈现一派虚弱之象:面色苍白或萎黄、神疲乏力、声低气短、汗出较多(气虚不固)、心悸怔忡(血不养心)。
其次是瘀血内停。手术创伤,必然损伤脉络,离经之血未能及时消散吸收,便成瘀血,阻滞于局部或经络之间。此即“术后必有瘀”。表现为伤口局部青紫、肿痛、刺痛固定不移,舌质可见紫暗或有瘀点。
第三是脾胃受损。此为术后调理之关键环节。麻醉药物、术后疼痛、情绪焦虑以及必要的抗生素等药物,首当其冲易损伤脾胃之气。脾主运化,胃主受纳。脾胃一伤,则运化无力,受纳不佳,临床常见腹胀、纳差、恶心、便秘或腹泻等症。脾胃为“后天之本,气血生化之源”,此源一竭,则气血无以化生,百药难以运载,一切补益皆成空谈。故曰:“术后调理,首重脾胃”。
再有就是阴津耗伤。手术失血、发热、汗出及禁食水等因素,均可导致体内阴液(津液) 的亏损。表现为口干咽燥、皮肤干燥、大便干结、舌红少津等。此“多虚”(气血虚、阴津虚)、“多瘀”(瘀血阻滞)、“脾胃弱”之类复杂状态,便是术后机体所处的病理基础。
术后调理,是患者从医院回归正常生活的重要桥梁。术后调理之目的,便是纠正此偏颇状态,促进机体全面康复。药食兼用,缓图其功:药食两用之材,其性温和,作用持久,尤适于术后虚不受补、不耐峻药之体。可通过每日饮食,缓缓调治,润物无声,于不知不觉中培补元气,调和阴阳。
顾护脾胃,开门纳补:术后药膳设计,必以“开胃健脾、顾护胃气”为先导与贯穿始终的原则。唯有脾胃功能恢复,才能纳食、运化、吸收,使药膳之补力得以化为气血,输布全身。此亦乃“寓治于食”的中医智慧。
6
药膳辅助慢病改善,效用虽佳,然不可妄用。必谨守以下原则:
辨证施膳为核心所在。必须辨清患者之阴阳、表里、寒热、虚实及气血津液状态,方能对证施膳。如阴虚之体,误食温燥药膳,无异于火上浇油;阳虚之人,错服寒凉之品,无异于雪上加霜。
必须明确,药膳起辅助调理、改善症状、减轻副作用、巩固疗效之用,绝不能完全替代必要的药物治疗,纯正中医药的作用不可废弃。尤其病情急性发作或加重时,更应及时就医,遵医嘱用药。
性味平和,用量宜轻。药膳取药食两用之物,性味相对平和。用量不宜过大,贵在长期坚持,缓缓图功。切忌贪功冒进,堆砌名贵药材,反失膳食之本意。
是深刻理解“脾胃特性”。脾主升清,胃主降浊;脾喜燥恶湿,胃喜润恶燥。故调理脾胃之膳,务必遵循“通降”、“运化”的原则。切忌一味蛮补,堆砌滋腻之品,否则反而会加重脾胃负担。我常想,给虚弱的脾胃进补,犹如给久旱的土地浇水,必先松土,再缓缓润之,若直接大水漫灌,反而会板结更甚。
结语
随着疾病谱变化、老龄化社会到来和“健康中国”战略实施,药膳的价值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。现代医学模式正从单纯的西医崇拜心理中转变过来,人们越来越追求整体、自然、个性化的健康方案。药膳以其整体调节、身心同调、因人制宜的特色,完美契合了这一趋势。
药膳知识的普及,能有效提升全民健康素养,它超越了单纯的饮食范畴,升华为一种生命观,一种生活方式,一种于平凡日常中践行的健康哲学。它告诉我们,守护健康的至高境界,是“寓医于食”,是“防患于未然”,是与自然和谐共处。
来源:央视线
标题:“膳”养天年 薛应中
地址:http://www.yangshinews.com/yscj/82787.html